虽然语言诞生之初所满足的功能是明确沟通,但自言自语的行为模式似乎又赋予了语言其他的功能属性。在本文中,费尼霍将内化语言视作与自己内部不同意见的沟通,但内化语言又何尝不是一种归纳整理思路的强有效工具?回忆一下平日的阅读过程——文字往往先转化为内部语言,才能被大脑所吸纳。不过相比之下,更好奇的是没能来得及学习语言的婴儿,又是如何跟自己沟通的?

照镜子的女人。图源:Frederick Carl Frieseke/Wikimedia
语言是人类的标签——正是因为有了语言,我们才能够建立深度人际关系与复杂社会体系。不过,即便是在完全独处的状态下,我们也会用到语言——语言甚至可以塑造我们与自身的无声关系。英国达勒姆大学教授查尔斯·费尼霍(Charles Fernyhough)的著作《心声》(The Voice Within)回顾了“内部言语”研究的发展历史——所谓“内部言语”,说白了就是“脑袋里进行的自我对话”。
费尼霍表示,内部言语是与社交语言同步发展的。这一想法由苏联心理学家利维·维谷斯基(Lev Vygotsky)首先提出。维谷斯基在20世纪20年代研究儿童发展与心理学,他发现,孩子们在学习与他人交谈的同时也在学习自我对话。他们一开始会大声把想法说出来,最后则是内化到脑海中。
费尼霍写道,内部言语不会像口头语言那样,受到诸多条件限制。比如,在进行口头对话时,因为要用到舌头、嘴唇及喉咙,我们就必须保持一定的说话节奏。内部言语就不需要这种节奏,所以速度会快许多。书中引用了一项研究,该研究显示内部言语的平均速度是每分钟4000字——10倍于口头语言。另外,内部言语往往也会更加凝练——毕竟我们自我对话时完全理解自己的意思,因而不需要用完整句子。
(journals.sagepub.com/doi/abs/10.2466/pms.1990.71.3.1043)
不过,内部言语还是保留了许多口头对话的特点。在进行自我对话时,我们也许会想象在和别人交换意见,又或者我们就是在自言自语,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就不是对话了。我们的思想里有许多不同意见,它们会争吵、会协商、也会相互交谈。
“我们都是分裂的,”费尼霍写道,“没有一个统一的自我。大家心中都有无数个意见不同的自己,每时每刻都妄图创造一个明晰、统一的‘自我’幻象。”
我和费尼霍有过一番交流,主题有关三方面:这些持有不同意见的自己如何通过内部言语进行交流?研究这一现象的难度如何?这一现象对我们可能有哪些启示或帮助?以下就是我俩对话的精华版,略有删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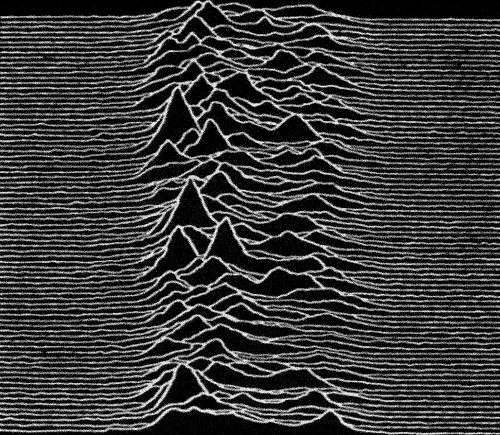
图源:tumblr
朱莉·贝克(Julie Beck):在您看来,内部言语和单纯的思考之间是否有区别?内部言语是否就是思考的一种形式?或者它们就是一回事,完全相同?
查尔斯·费尼霍:我觉得“思考”这个词很有迷惑性。思考的含义很广,囊括了许多不同的东西,而我们常常不能准确理解我们在使用这个词时究竟想表达什么。因此,我尽可能避免使用这个词——当然这很难。不过,这个词确实有点像是指我们的一切思维活动。有一种思维方式称作言语思维,本质上说,那就是内部言语,也即我们用词语在脑海中进行思考。不过,我可以肯定的是,即使不借助语言,你也可以相当聪慧,也可以拥有许多聪明的想法。婴孩每天都在证明这一点;动物们也同样每天都在证明这一点。
贝克:研究这一现象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困难:只有自己才能真正准确地理解用内部言语表达的想法。所以研究人员想出了什么应对之策呢?
费尼霍:这确实很棘手,并且当我开始做这项研究的时候,这还是个比较冷门的领域,没有太多东西可供参考。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间,苏联方面进行了一些相关研究,但出于某些原因,西方世界在这个方面的研究并不多。我们不可能直接进入被试的脑海、阅读他们的想法,我们只能要求被试把自己的想法报告上来。麻烦之处在于,观察内部言语这件事儿本身就会影响内部言语的产生过程。
长久以来,人们总是说,我们这种研究意识的方法并不合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太容易被外界扭曲了。我要说的是,在过去的大约20年中,这种情况已然开始改变。现在,人们更多地把对意识的研究当成一种问询的科学主题。并且,人们在研究诸如内部言语这样的课题时,掌握的技巧越来越高明了。
观察一下小孩玩玩具时的场景,你很可能会看到她在自言自语。
我们注意观察人与人之间的个体差异、人们使用内部言语的频率以及内部言语与人们认知特性之间的关系。我们还可以看看,如果不让被试使用语言系统,会不会影响到他正努力完成的主要任务?要阻隔语言系统不难,只需向他布置一个次要任务,比如让他不停地重复一个单词。剩下的事儿就简单了,你可以直接询问被试,可以给他一份调查问卷,可以使用各种经验采样方法。另外,借助新技术,你还可以看看人们在进行内部言语时,脑海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贝克:显然,人们报告上来的他们进行内部言语时的状态和行为会千奇百怪、各不相同。但是,您是否能够从中发现一些内部言语的主要性质或普遍特质?
费尼霍:我们已经开始意识到,内部言语涉及许多方面。我觉得,以前大家将内部言语单纯地假定为一种形式的独白:一个孤独的声音在脑海中响起,随后便唠叨起来。而现在,我们则认为内部言语有几种主要形式,根据其精简程度、浓缩程度而各有不同。我们觉得,内部言语间的差异还体现在,其与真实对话(当与不同观点碰撞时)的相似程度。我们正在着手梳理这些不同性质,并且这也和内部言语拥有许多不同功能这个观点不谋而合。内部言语与自我激励、情感表达有关,并且很可能还有助于我们从自我的角度了解自己。
贝克:我们再多聊一会儿内部言语的各种目的,或者说各种作用吧。我能想到的一个常见的例子就是在体育运动中,人们总是通过自我对话来提升竞技表现。人们还会出于什么原因使用内部言语呢?
费尼霍:如果你了解维谷斯基的理论,你就会知晓,内部言语其实是一种我们过去常常大声说出口的语言的内化版本,而这正是它存在的原因。小时候,我们参与社交对话,与他人交谈,并且还会经历一个名为“私密言语”的阶段,正是在这个阶段中,我们会大声地自言自语。之后,这种行为就完全内化了,所有的一切都会在脑袋里以无声的方式进行。维谷斯基认为,这种自主语言拥有各种功能,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为了盘算下一步行动。观察一下小孩玩玩具时的场景,你很可能会看到她在自言自语。有时候,她会说些不相关的东西,但更多的情况是,她会说,“我要造一条铁轨”,或是“我要造一座房子”,或是“这房子看上去要和阿姨的房子一样”,又或是别的什么。这其实是一种解说词,明显能够帮助她想清楚自己现在正在做什么,并且帮助她规划接下去要做什么。
不过,我们同样也会用内部言语反思过去。内部言语有想象功能,可以让我们在脑海中创造出与现实不同的情况。它还有一些自我激励作用,就像你常常在体育运动中看到的那样。在竞技体育中,人们既可以用这个方法让自己兴奋起来,也可以以此自我责备。他们做了蠢事之后,便会用私密言语训斥自己一通。而我认为,其实我们大家都会这么做,只不过体育运动更加强化、凸显了这一点。

图源:Giphy
贝克:所以,我总是在大声地自己对自己喊话,也总是在脑海里自言自语。您刚才提到,维谷斯基的理论大概就是说,我们孩提时代经常做的事,也就是大声自我对话,后来内化进了脑海里。就拿我自己来说,我还是会像小时候那样在房间里晃来晃去,嘴里嘟哝着:“钥匙在哪儿,好的,在这儿,手机找到了,钱包也找到了……”您觉得这个过程和内部言语是否相似?这种行为究竟是大声说出口的还是内化于脑海中的?
费尼霍:我完全没有理由认为这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小时候常常实践的那种私密言语。只不过,作为成年人,在某些特定的情形下,我们会发现把这些话大声说出来真的要比在脑海里空想更有用。话一说出口,声音就会迅速在空气中产生回响。这样确实更真实一些,更方便你记住刚才说的话,因而也更易于形成记忆。
如果我们的祖先总是在灌木丛里喃喃自语,剑齿虎不会让他们活很久。
我想大胆提出这么一个猜想:大声地自言自语时面临的困难,会比通常情况下难度更高一点、压力更大一点或者挑战性更强一点。我觉得当事态严峻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尤其容易大声地把问题讲出来。这也当然和小孩进行私密言语的模式相符——当形势变得更加困难时,他们自言自语的频率会更高。
成年人也自言自语这个事实暗示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维谷斯基的理论。尽管我们脑海中的内部言语最初发源于社交语言,之后又发展出了这种大声说出口的私密言语,但当这种语言内化后,还是有可能脱口而出,显露于外。内部言语不会永远埋藏在脑海中,这并不是一条有去无回的不归路。大部分人都会自言自语,但这种行为在社交上还是有些尴尬。
从进化的观点审视一下我们这种行为的成因,应该是颇有意义的。当我们学会了语言并把它运用在说出口的私密言语中时,我们也很快意识到了这点:身处困境、险境之时,大声地自言自语绝不是什么好主意。如果我们的祖先总是在灌木丛里喃喃自语,剑齿虎不会让他们活很久。此外还有一些社交上的、文化上的压力。如果你到处散布你的所思所想,你的竞争者、对手以及周围的其他人都会知道你在想些什么,你的计划便难以实现了。因此,我们确实有必要悄无声息地完成这种自我对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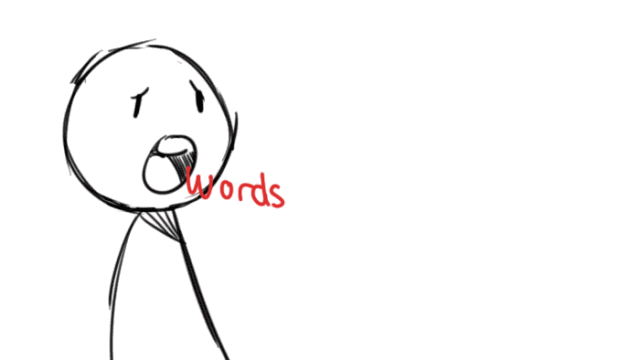
图源:Art of Marina Khatin
贝克:当然,如今大多数我们进行自我对话时的环境不会有那么极端。好玩的是,我发现我总是在杂货店大声地自言自语,就是因为在购买食物时,所有人都会看着我,让我紧张不已。
费尼霍:尽管这么一段自我对话是针对个人自身的,但似乎他人的存在才是这段对话的诱因。当和别的小孩儿待在一起时,孩童身上更容易出现你这种自言自语的情况。并且我觉得背后的原因可能可以推广到成年人身上——如果你身处一个别人都在喃喃自语的环境中,你可能也会这么做。我在超市里也会自言自语,但这是因为我想记住购物清单上的每样东西。
贝克:不然的话,你就啥也找不到了,尤其是当商品不在它原来的货架上时。
费尼霍:一项设计巧妙的研究证明:购物时来一小段自我对话确实有助于你做这件事儿——从排列整齐的一列列超市货架上取下你想要的商品。这是现已证明了的自我对话的好处之一。
(www.sas.upenn.edu/~swingley/papers/lupyanSwingley_qjep11.pdf)
贝克:您刚才说,维谷斯基的理论提到,我们在学习社交语言时,也在学习内部言语。能为我详细解释一下,口头语言和内部言语这两者的发展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吗?
费尼霍:嗯,维谷斯基认为这两者在婴孩时期是统一的。人类在这一时期便已发展出了基础智力,这点从一岁大的婴儿身上我们就能看到。他们已经有能力做各种事情,包括做一些基础动作、做点小事儿、记点小东西。不过,这只是学会说话之前的智力——也就是所谓的“语前智力”。发展出语前智力之后,语言能力就不远了。大多数儿童学会说话的速度相当惊人。这里的重点并非你的思维需要语言,而是语言能力的出现必然大有益处。它改变了你的思维方式,并且提供了另一种行动方式,因为言语本身就是一种工具。大约到了2岁的时候,语言就会和智力协同发展,并一起迎来一次大幅提高。这个时候,某些真的很特别的东西诞生了,而且这有可能是宇宙中独一无二的。
其实,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语言也并非必需,你可以使用手语,或者别的任何语言。很多人会问:“聋人怎么思考呢?”我会这么回答:“嗯,他们自有自己的语言。”已有很多证据表明,有的人拥有一种内化的符号对话系统。他们可以用这些符号来规范思维,正如我们对口头语言的使用一样。
有意思的是,不同的聋人有不同程度的语言接触。有些人是生来就全聋的,而有些人则还保有一点听力且能接触到一点语言,还有的人是在孩提时代丧失听力而非生而如此的,各种情况不一而足。所以你应该能想到,聋人的内在言语各不相同。有些具有一些语言体验的聋人会告诉你,他们的内部言语要更“有声”一些,也就是很可能更像你我这样的正常人的内部言语。但另有一些聋人会告诉你,他们的内部言语很大程度上更像是一种符号语言,更像是一种视觉化产物。
贝克:您把内部言语形容为一种对话。如果这确实是在两个意见不同的自我之间进行的,那么这两个分裂的自我又是如何在我们脑海内部工作的呢?是不是就像陈旧的弗洛伊德理论那样,超我警告本我:“不要吃甜甜圈。”
费尼霍:有点儿那个意思。问题的关键在于自我的多重性,也就是说,我们的自我有各种不同的部分。无论你是否想要用弗洛伊德理论解释内部言语,都是可行的,但那不是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方向。最重要的是,内部言语包含说话与倾听这个基本的对话模式。倾听者既可以是你自己也可以是别人。比如说我现在就可以和我妈来一场内部对话。有一些人告诉我,他们常年和一些不在现场的人进行内部对话,对象可以是已故之人,可以是虚构的人物,也可以是上帝。在本书中,我尝试从这个角度重新思考精神冥想和祈祷的本质,那就是和另一个人进行对话。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现有对话结构的诞生要归因于我们在孩提时代发展出来的各种能力和模式,而这种对话结构让一切都成为了可能。这是因为,内部言语是我们内化社交对话的产物,我们将对话结构植入其中,进而让其成为了思维核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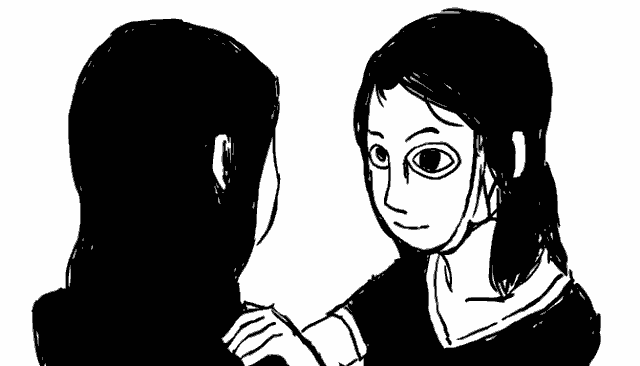
图源:Tobias Sallewsky
贝克:总的来说,人们并不擅长汇报他们脑海中所思所想的细节,对吧?
费尼霍:我们采用描述性经验取样(Descriptive Experience Sampling,DES)的时候——即要求被试口头报告他们自己的内部言语体验——会假定被试所作的许多描述,都是他们自认为脑海中所想的东西的某种归纳,而非真正出现在他们脑海中的东西。并且,这也是为什么DES能够让被试大吃一惊的原因。有些被试会觉得他们的想法有一点消极,但事实却证明是相当令人愉悦的。反之亦然。这真是一个有趣的哲学问题,因为它表明,我们可能会被自己的经历所误导。想想我们可能连自己脑子里的真实想法都弄不清楚,那可真够疯狂的。
(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1097-006-9024-0)
贝克:所以,人们可能对自己的个性和思维模式有一些思维定式,然后发现这也许并不真实?
费尼霍:没错,完全正确,而且这甚至能够解释心理问题的某些特定方面。在拉斯·赫尔伯特(Russ Hulburt,DES的发明者)的一篇论文中,有一个强迫症患者的案例。在这个案例中,赫尔伯特写道,这位病患抱怨自己的脑子里总会产生一些烦人的强迫性想法,但当赫尔伯特给他做了DES测试后,他发现这些想法其实并没有那么多。
贝克:也许他只是更容易注意到这种情况?
费尼霍:是的。所以,我认为事实的真相是,我们对自己的体验作了许多一般性的归纳,形成了一种自我理论方法。而这种方法并不总能匹配上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尝试捕捉的真实情感。
贝克:那么,我们怎么用这个理论解释那些幻听现象呢?
费尼霍:这个现象倒不难解释。大多数情况下,幻听是一种很压抑的体验。它通常与重度心理疾病联系在一起,还会表现出许多不同的精神病症状。对精神分裂症患者来说,幻听现象也并不罕见。另外,许多没有心理疾病的人也会产生幻听现象。在人生的某些节点上,很多人都会有一些相对短暂的或是一次性的幻听体验。
幻听现象可以让人很压抑,但有时候给人的感受会缓和得多,甚至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幻听反而具有积极向上、催人奋进的指导性作用。这里的重点在于,当人们出现幻听现象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在产生一些内部言语,但由于某些原因,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些话语实际上是他们自己产生的。幻听的体验就像是某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从外部进入了自己的脑海。
这个说法也有许多问题。很多幻听的人都拒绝接受幻听就是他们自身的内部言语这个说法。由于幻听的内容通常是那么的令人不悦,所以幻听者对这个说法会感到十分痛苦。另外,幻听还牵扯到其他一些因素,记忆似乎就是其中影响颇大的一种。幻听通常和一些创伤事件联系在一起。那些创伤事件好像就以某种方式改头换面地重新进入了意识之中一样。所以,任何有关幻听的解释都必须以某种方式考虑记忆的因素。我们认为,幻听现象也许也分很多种,我觉得不太可能只有一种幻听模式。

图源:Soren Dreier
贝克:您在书中写道,“另一个内部言语可能起重要作用的领域,便是我们关于对和错的思辨过程”——我知道现在其实还没有任何相关研究,但我想听听您怎么思考这个问题。我们自我对话的方式,或者说我们在脑海中质问自己信仰的方式,会怎么影响我们的道德判断?这就是我们改变想法的方式吗?
费尼霍:我在身处进退两难的境地时会自己和自己说话。虽然这样的困难情况绝不止一种,但我确实经常在面对可能是道德方面的问题时作许多自我对话。我赞同这么一个观点:那些在认知方面有用的工具也会在我们思辨道德问题时发挥积极作用。当然,很多有关道德的思考都是未经深思熟虑而下意识作出的情感化判断。不过,你要是跟我说,我们证明了在某种特别形式的道德思考中,语言起了大作用,那我也不会很惊讶。
如此种种其实都包含了一种基本要素,它和直觉有关。我确实在很多情况下都倾向于相信我的直觉,因为我觉得我的大脑在对问题进行加工,我在做一些智力工作,但这也许不是有意识进行的,也许不是任何我能用言语表达的东西。不过,我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对于许多不同方面的问题,通过内化的彻底思考、彻底讨论的确很有帮助。这就像我们和朋友一起讨论工作确实有用一样,部分原因是我们可以把问题和想法用语言表达出来,可以进行有益的对话,可以来来回回地从各种视角考虑问题——这真的特别有用。甚至,仅仅就是把问题和想法大声说出来这件事本身,也有不可思议的巨大帮助。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利维坦):为何我们会自言自语?

